4月10日下午,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茶座迎来一位风尘仆仆的客人。刘涛,是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及社会学研究所教授,长期在西方语境中关心中西比较问题,具有宏大视野。今天,他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宏大叙事的话题——《宏大叙事的零和或融合?中国模式中的西方角色》。在世界风云变幻,欧美传统宏大叙事纷纷捉襟见肘,德国深陷中东移民问题的当下,这个题目尤其引人瞩目。

讲座的叙述本身也比较宏大。第一个标题是:“西方叙事的终结?中国叙事世纪的来临”。他首先介绍了国际形势:特朗普要脱离全球化,英国脱欧,苏格兰要脱英,欧洲陷入难民危机,欧美右翼崛起,伊斯兰国猖獗,俄罗斯介入西方大选,中国崛起并且有“回到新民主主义”重新开始民族主义阶段的趋势……
这是一个中国叙事世纪吗?他认为,近代以来,中西互为观察的镜像,或者理想化,或者妖魔化。比如法国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当作理想世界,而发现中国衰落之后,到了黑格尔那里,中国已经成了负面形象。
他介绍了一本德文书籍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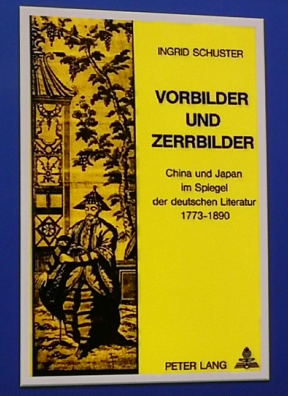
可以译作:《从榜样到走样》
反过来也一样,西方形象在中国也有一个曲折的反射过程,从鸦片战争之后的向西方学习,到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知识界对西方幻想遭遇破灭,再到今天的复杂形势。
总体来说,中西实力对比的变化影响中西双方的互认,但是要考虑政治等其他因素,并非线性关系。比如文革的时候,中国状况不好,但在西方反而形象好。因为那时候中西要联手对抗苏联。1990年代中国在西方形象比现在好,显而易见,经过二十多年大发展,中国现在各方面状况比1990年代好得多,但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反而差了。
最近在德国观察到的形势是,因为特朗普上台,反全球化,德国媒体开始对中国积极报道。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力主全球化,德媒详细报道,是10多年来所未见。
西方是中国崛起路上甩不开的镜像和影子
刘涛老师是黑格尔主义者。就像上和下,左和右,看似对立,但是组合在一起,恰恰构成了坐标。中和西存在辩证关系,互相参照,无论理想化还是妖魔化,说明都在一个坐标系里。德语表述东方和西方的词汇很有意思:morgenl und abendland ,morgenl是日出之地的意思,abendland是日落之地的意思。大陆的东端与西端,日益联系在一起。完全不同则没有沟通,能进行沟通,仍然有一个共存的话语体系。
在中国模式语境下解构西方是必要的,建立中国模式离不开解构西方,但仅仅停留在解构则是完全不够的。对立的另一面是统一,冲突镜像的另一面是共存,解构的另一面是融入,修辞寓意的争辩反映出参照系数趋同。
解构的目的是建立独立的自我,精神自由的自我,而不是要除去外来文化中合理的成分。解构的目的不能停留在解构上,而是要着眼于建构。修辞的论战只是要破除元叙事的霸权,而不是“逢西必反”。
德国总理默克尔有一句名言:“伊斯兰文化是德国的一部分。”她认为,如果试图把异质文化彻底排斥出去,其后果很可能是完全的社会撕裂。因此,关键看你怎么去建构。事实上,默克尔的这句名言一经说出,马上就引发争议。其实,她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治理的智慧,即宗教的非政治化。
他又举了甘地的例子。在印度现代化历史上存在着甘地的难题和印度精英的困惑。印度精英接受了英国殖民统治教育,当他们争取印度独立,去殖民化的时候,使用的文字工具还是英文。他们为此感到困惑:这是不是耻辱?要不要去掉英语?甘地认为,英语是工具,你可以依附它,也可以用它来争取印度民族精神自由。
由于英语的统一,印度南北婆罗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直接沟通了。
所以要区分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。
文化、社会综摄模式
刘老师以中国古代宗教为例,提出了文化综摄主义。比如佛教传入中国,被中国化了,儒释道合流。而今天,中国在社会发展模式中也采取了综摄主义。比如高铁,就是综合了多国的技术思路。
我们需要打破所有的工具箱重新来过吗?显然不可能。离开了来自西方话语的舶来品,我们几乎无法完成一场完整的学术对话。社会科学工具箱里,几乎所有的词语、概念、理论和方法论都来自于西方。So what?没关系,要使用这些工具,创造自己的故事。中共一直具有实用主义精神。中国人一直富有学习精神。我们不妨大胆的说出来,西方文明是中国现代文明的一部分,但也就是一部分而已。
中国的全球化
我们无需再来一场颠覆西方文化的“五四”。完全的破立不可取,在现有基础上的话语叠层建筑更理性。当代的我们更需要统摄主义。赞同郁建兴的一句话:中国模式要抵制特殊主义的诱惑。我们解构西方神话,解除奴性,解除西方元叙事的霸权。但不解构西方现代文明。解构当中也不能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大量问题。
我们要追求全球化的中国和中国的全球化。西方叙事和中国叙事需要融合。中国应当逆转“逆全球化”。中国不应当停留在世界的一角孤独地论述自己。中国模式必定是全球模式。提倡“世界社会”这样一种新的叙事方式。
茶座互动环节比较热烈,大家各自提出了不同观点。
张维为教授接过印度的话题:尼赫鲁最能交心的人是自己的英国同学,而不是印度人。相对于印度的诸多语言,汉语更具有独立性。张教授尤其强调语言对个人或民族思想独立性的深刻影响。譬如,邓小平当年法语就没有学好,现在看来反而是好事——正因如此,他才获得以中文和中国文化为本的思维观。相比之下,印度所谓的“英文优势”可能恰恰是其弱势。
范勇鹏研究员认为:每个文明的出发点不同。中国认同相对客观,“远人不服,则修文德以来之”,西方各国则强调派他性。默克尔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不符合历史。欧洲大陆是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,各文明并行,在互相排斥中确立自我。而中国文明定义不依赖外来者参照,比如不需要先定义日本才能定义中国。欧洲则需要他者。亨廷顿引用了这样的观点“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,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。”施米特则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划分敌我。1492格拉纳达战役,基督教战胜穆斯林,那一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,发现了比自己低的文明,西方才建立起自身的文明神话。西方人很难接受中国的统摄主义。郁建新反对中国的特殊主义,但我们首先要破除西方特殊性和西方话语体系。
吴新文教授则认为,普遍和特殊原本就不能割裂。没有特殊,就没有普遍。而逆全球化是在哪个层面?国家层面还似乎国际资本层面?在后者,全球化从来没有逆行。
文扬研究员认为,中西互为镜像,过去是这样,现在则不是了。在对方的话语语境下思考问题,会无法辨识问题。即便是中国国内问题,如果套用西方话语来看,反而解决不了问题。
余亮副研究员认为,今天参与讨论者,平时直接面对本国的话语斗争现场,所以会有不同看法。但是刘涛老师处在德国语境下,面对不同的问题,体现出的自信心能够感受到。不过谈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时候,就像吴新文老师说的,要区分是哪个层面上的全球化。逆全球化是口号、情绪还是事实?反西方化是口号还是事实?如果不是事实,那就是伪问题。
最后,刘涛教授做了回应,他认为不仅西方有他者论,中国古代也有华夷之辨,有认同和认异。讨论话语,不要拘泥于细节的编码,要更关注总体性和话语实践,和平建设我们的话语体系和发展模式。
(中国研究院 余亮 报道)

